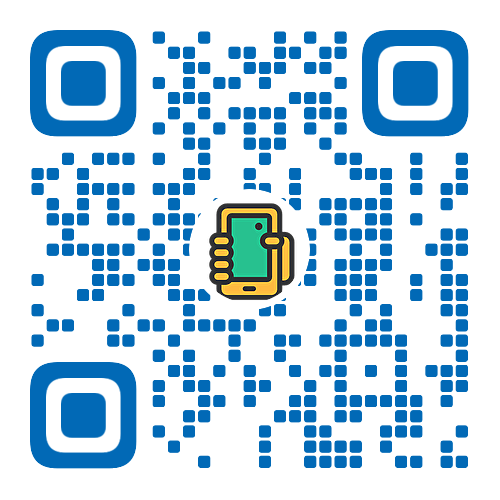滾動信息:
滾動信息:編者按
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,本報記者循著歷史足跡,尋訪參與和見證這場深刻變革的親歷者,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和鮮為人知的故事,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太倉40年來發生的滄桑巨變。
□本報見習記者 王 俊
親歷者名片
顧建平,香塘集團董事局主席,1944年生,1983年創辦太倉香塘鞋廠。他一手把這家小廠打造成為年銷售收入超80億元的多元化集團。他見證了太倉鄉鎮企業的崛起與轉型。
萬里長江經太倉奔騰入海,幾十年浪濤激蕩間,涌現無數弄潮兒,香塘集團董事局主席顧建平就是其中一位。
站在新啟用的香塘大廈最頂層,臨窗遠眺,顧建平看到的是車水馬龍,想到的是崢嶸歲月。
一個拖鞋王國的誕生
凡成功者,必敢為人先。
1976年4月,32歲的香塘村大隊會計顧建平,一咬牙,接手了多年沒有效益的大隊辦預制件廠。
“僅靠種田算賬,日子好不起來!”這是一個農民的勇氣之源。
顧建平打理下的預制件廠,只能澆筑一些農村蓋房用的水泥構件,兼為沙溪水泥廠搞供銷。因大環境不好,預制件廠兩三年后依然沒有一點起色。
1978年底,一聲春雷響徹神州大地。千千萬萬像顧建平一樣的人,敏銳地察覺到,干一番事業的機會來了。
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,1980年初,顧建平另辟蹊徑,在香塘村辦起了繡花廠。一開始,繡花廠效益不錯,但因管理不善,還是以失敗收場。
兩次失利,顧建平并未氣餒。經過反復調查,他發現將繡花業務轉為做繡花拖鞋,或能闖出一片新天地。
于是,1983年,香塘繡花廠更名為太倉香塘鞋廠,專門生產工藝拖鞋。
“當初我們一無資金,二無技術,三無設備。”顧建平回憶,他和16名職工一起將大隊5間養鴨的草房改為廠房,去上海聘請一位做鞋師傅,又湊了450元錢買來3臺報廢的舊設備,將鞋廠張羅起來。
買舊設備這種在今天看來無比簡單的事,在當時可是個棘手問題。因國營企業管理嚴格,即使報廢設備也不能出省界,上海的鞋廠無法直接將舊設備賣到太倉。
后來,上海方面想了個法兒,先把舊設備賣給滬太交界處的廢品收購站,再由顧建平從廢品收購站買回,才解決了香塘鞋廠的燃眉之急。
香塘工藝鞋面料時尚、款式新穎、做工精良,甫經推出,便成搶手貨,到1988年,年銷量突破100萬雙。
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,外貿風生水起,顧建平抓住機會,一舉將香塘工藝鞋推向日本、韓國等市場。到2000年底,香塘工藝鞋年產能已達4000萬雙,95%以上出口。
這一年,香塘鞋廠成為資產總額達3億元、擁有職工2000多人的國內最大工藝鞋生產出口基地。
也是在這一年,以香塘鞋廠為根基的香塘集團,通過改制,轉為民營企業,掀開了發展新篇章。
一家鄉鎮企業的轉型
不謀全局者,不足以謀一域。
當鞋廠鼎盛期年盈利3000萬元時,顧建平卻意識到: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旦過了紅利期,在太倉立足就會越發艱難,唯有轉型才能可持續發展。
新世紀,在香塘集團的棋盤上,顧建平下了三手棋:化纖、生物醫藥、金融投資。
顧建平想辦的化纖企業,不是“小打小鬧”,而是上規模、設備先進、向全國第一方陣看齊。
一個做拖鞋的,也敢“染指”高技術含量的現代化纖?許多人覺得顧建平冒進了。
“自己不懂不要緊,可以聘請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。”顧建平看中的是現代化纖的良好前景以及本地市場。為了穩妥起見,他選擇與沙溪的金輝化纖有限公司合作,雙方共同成立了振輝化纖有限公司。
振輝化纖于2005年投產,并于2006年上馬了二期工程。雖然振輝化纖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創,最多一個月虧損了3000萬元,但我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得力,市場轉好,僅2010年振輝化纖就賺了2億元。
同一階段,香塘集團的制鞋業務不斷收縮,與化纖業務一消一長,使自身實現了第一輪轉型升級。
顧建平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投資,也是大手筆。2002年,香塘集團通過與北京昭衍新藥研究中心合作,組建了舒泰神(北京)生物制藥股份有限公司。
生物醫藥產業投資規模大、周期長、回報慢,當時不被普遍看好。但顧建平認為,生物醫藥是國家大力支持倡導的前沿高科技產業,縱然投資不會立竿見影,但它的前景非常值得期許。
十年磨一劍。2011年,舒泰神成功上市,為香塘集團帶來豐厚回報。同年,香塘集團參股25%的昭衍(蘇州)新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沙溪開業。2017年,昭衍新藥成功上市,香塘集團再下一城。
繼昭衍之后,香塘集團又投資入股了思坦維、金盟生物、金普諾安等多家生物醫藥企業。同時,伸出“資本觸角”,先后創辦擔保公司、小貸公司等,參股商業銀行、進軍地產,實現了實體產業與金融產業的融合發展。
在那一記春雷轟鳴過后的第40個年頭,香塘集團已經發展成為擁有20余家子公司、總資產達70億元、年銷售收入超80億元的地方標桿型企業。
“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。”顧建平由衷地告訴記者。
- [04-27] 蘇州元亮食品有限公司企業名稱變更
- [04-22] 2025年五一勞動節放假通知
- [04-08] 陽光智能簡歷分析系統1.0使用說明
- [04-01] 2025清明節放假通知
- [03-25] 太倉市婁東賓館有限公司擬錄用人員公示
- [03-20] 太倉市婁東賓館有限公司擬錄用人員公示
- [02-25] 太倉市婁東賓館有限公司擬錄用人員公示
- [02-14] 太倉市婁東賓館有限公司擬錄用人員公示
- [01-22] 2025年春節放假通知
- [12-25] 2025年元旦放假通知
- [12-11] 關于瑞宏精密電子(太倉)有限公司問題反饋的積分獎勵公告
- [11-28] 太倉市婁東賓館有限公司擬錄用人員公示
- [11-13]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2025年部分節假日安排的通知
- [05-17] 太倉泰納達汽車部件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6] 太倉東泰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6] 蘇州芳科實業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4] 蘇州鑫睿達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3] 蘇州富日智能裝備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3] 2025年蘇州太倉市教育系統公開招聘備案制教師公告
- [05-13] 太倉市同維電子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2] 蘇州巨能發電配套設備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2] 藍探科工業自動化(江蘇)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2] 蘇州太倉寶龍大酒店有限公司太倉寶龍福朋酒店招聘簡章
- [05-12] 雷勃電氣(蘇州)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10] 太倉市新英工業燃燒設備有限公司招聘簡章
- [05-09] 蘇州長锜塑模制品有限公司招聘簡章